在作家茹志鹃诞辰百年之际,上海芭蕾舞团以近乎奢侈的主创阵容,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小说《百合花》搬上芭蕾舞台,为红色经典的当代改编提供了全新范本。茹志鹃之女、著名作家王安忆执笔编剧,编导王舸领衔,集结杨帆、萧丽河、崔晓东等顶尖艺术家,这场创作不仅是舞剧向经典的致敬,更是再次彰显海派文艺强大的兼容性和创造力。
这是跨越时空的美学对话——当海派芭蕾的细腻肌理遇上革命叙事中的人性微光,茹志鹃笔下那朵“不合时宜”的百合,终于在海派艺术的土壤中绽放出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从“军民情”到“青春祭”
对绝大多数观众而言,王安忆和她的《长恨歌》早已根深蒂固地成为上海的时代符号和文化情结,她的母亲茹志鹃虽不算陌生,但其代表作《百合花》并非容易为当代观众所理解。
短篇小说《百合花》诞生于1958年,那正是革命文学的高潮时期。该作却以其含蓄、细腻的笔触,在宏大叙事中开辟了一条幽微的情感小径。这个看似以“军民鱼水情”为主题的小说,并不同于同时代的《柳堡的故事》等作品,后者充满着时代热情和热烈奔放,以直白歌颂和明朗爱情为叙事特色。茹志鹃的笔触始终游弋在政治话语的边缘——她写通讯员羞涩的耳根通红,写新媳妇新婚被子上的百合花,写文工团员“大姐”欲言又止的凝视。这些细节构成了一曲未被时代淹没的青春私语。
《百合花》中含蓄的情感表达与特殊的时代语境为当代观众设置了理解门槛。故事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借被子”这一个贯穿事件,就将通讯员、新媳妇和文工团员“大姐”三人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感互动呈现出来:既非明确的爱情,也非纯粹的军民情,而是一种混杂着羞涩、怜悯与青春生命共鸣的复杂情绪。这本是文字间擅长流转的诗意与韵味,艺术中追求的超然与幻想。这于革命文学时代,本就如骄阳烈日中吹来的一缕春风,弥足珍贵却又格格不入。
作为红色经典,如何在当代充分发挥其经典价值,让观众获得更准确科学的时代共鸣与精神对话,本身具有极高难度;作为舞剧改编,如何在舞台上完成战争书写的诗意转化、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学优势,也具有不同于以往舞剧文学改编之作的挑战。
王安忆在执笔舞剧版本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质,因此选择将主题从集体叙事转向个体生命体验,例如为舞剧新增了“大姐日记”的画外音片段(选自茹志鹃其他作品语句),使其成为贯穿全剧的“当代解说者”。

舞剧的开场是从一个当下的舞蹈排练场开始,排练厅上方赫然的时代标语“人民文艺为人民”,看着青春活跃的芭蕾舞演员们正在排练,人到中年的“大姐”以叙述追忆回到小说中的1940年代。通过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那赋予充沛情感的声音,观众被自然代入进一段个人记忆中,以个人化的情感和视角去体验一段战火纷飞中的独特青春记忆。个人化的叙事,不但可以规避舞剧不便以复杂叙事来完成宏大主题的特质,还将原小说的叙事重心从政治话语转向更具永恒性的生命体验。这样一种双重跨度和空间角色的设计,就让当代观众更容易代入——观众随着“大姐”,在历史的缝隙中窥见一段被战争掩埋的青春。
从“时代激情”到“生命本真”,上芭独具眼光地选取了《百合花》作舞剧改编,在革命外壳下找回了文学最珍贵的体温,为舞蹈找到了温柔而丰富的注解。

海派美学的当代调和
如何让苏北农村的故事与上海气质共鸣?舞剧给出的答案是:以海派的精致美学解构具体地域符号,在抽象中抵达普遍。将一部农村革命叙事,转化出田园气息和浪漫情怀,使其成为具有当代美学语境的舞台诗篇。
舞剧《百合花》的难题在于它要如何用芭蕾这样一个具有西方特质的艺术形式来呈现民族特色和当代审美。小说故事中的时代背景为1946年解放战争的一个农村,据考证写到的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江苏海安这一块土地上。同样为战争背景的题材,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巧妙借助特殊的时代与场景,充分利用民国海派文化和上海都市的繁华空间来适应现代舞的气质,展现能够最贴合现代舞特质的内容,如“渔光曲”和旗袍舞等。然而,《百合花》的故事空间发生于中国农村,对芭蕾的艺术特质而言,这种差异必须要弥合。海派文化则在解决这一创作难题中再一次起到了当代调和的价值。创作者首先淡化苏北农村的地域特征,代之以更具普适性的海派审美。

新媳妇的嫁衣摒弃传统写实的红袄绿裤,改用藕荷色真丝绡面料,并融合了民国旗袍与当代芭蕾练功服线条,既有视觉上的优雅,也兼具了表演上的实用性。这种“去民俗化”处理,让角色从“农村小媳妇”升华为永恒的女性形象。拟人化地用多个演员来呈现百合花曼妙的姿态与诗意的摇曳,尤其是作为回忆过去的空间,色彩朦胧而温暖,成为全剧的一个突出亮点。
舞台的空间设计突出诗意空间,大部分场景摒弃了写实的农家院落,代之以倾斜的木质平台。中秋之夜,上升的月亮占据舞台背景的最中心,柔和的月光唯美地衬托着人性的美好。乡野田间和排练厅场景自由转换,为剧情的展开提供多样化的空间规定情境。而在展现通讯员牺牲的战争段落空间里,舞台上以非常写实的方式来展现战火硝烟。除了影像中极度逼真的战火与号角,舞台上还有满是鲜血的战服、印着红十字的医院隔帘等,与前时空中以虚拟唯美来展现人性美好时空呈现鲜明对比的场景。通过角度变换和灯光色彩的配合,时而是农村田野的暖色光影,时而是野战医院的冷蓝投影。这种"一景多用"的简约美学,既延续了海派戏剧"以少胜多"的传统,又符合国际当代舞坛的极简主义潮流。

在音乐方面,创作者以交响化的语言为基础,尝试还原芭蕾舞蹈艺术中最本真、传统的表达方式。同时,兼顾民乐、民歌等民族元素作为内核,力求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尤其是通讯员羞涩地向新媳妇借被子、新媳妇幻想新婚丈夫牺牲前在家时的几个场景,以相对简约的舞蹈语汇而更突出音乐对心理情绪的抒写,很好地把握了茹志鹃在小说中强调的诗意化情绪。在这种巧妙的虚实之间,创作团队整体上很好地把握了作为一部以革命文学和现代题材为蓝图的舞剧创作的要领。
《百合花》舞剧创作团队以海派美学为桥梁,成功实现了三重跨越:在西方芭蕾形式与中国农村题材之间,找到了诗意对话的可能;在革命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诉求之间,建立了情感共鸣的通道;在具体地域特色与普遍人性表达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这种调和不是简单的风格拼贴,通过解构具象的地域符号,保留最本质的情感内核。通过融合东西方的艺术语汇,创造出具有当代性的舞台语言。
然而,从芭蕾舞的美学艺术来看,也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如全剧最重要的象征——百合花被子,舞台上完全还原了小说里描写的那条"枣红底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与整体舞台的风格,以及演员的服装设计相比,给观众的视觉审美还不甚协调。是否需要在剧中从一而终地将这条被子高度还原,是否也可以处理为曼妙轻纱一般,使其真正成为那个时代一群有着美好青春和理想的年轻人的写照?也由于被子的设计与处理过于写实,当通讯员、新媳妇和“大姐”三人围绕被子而起舞时,也就不免让观众觉得费解,甚至误解,从而破坏预期的审美。


(程姣姣,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助理研究员)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海派艺术土壤让这朵“百合花”绽放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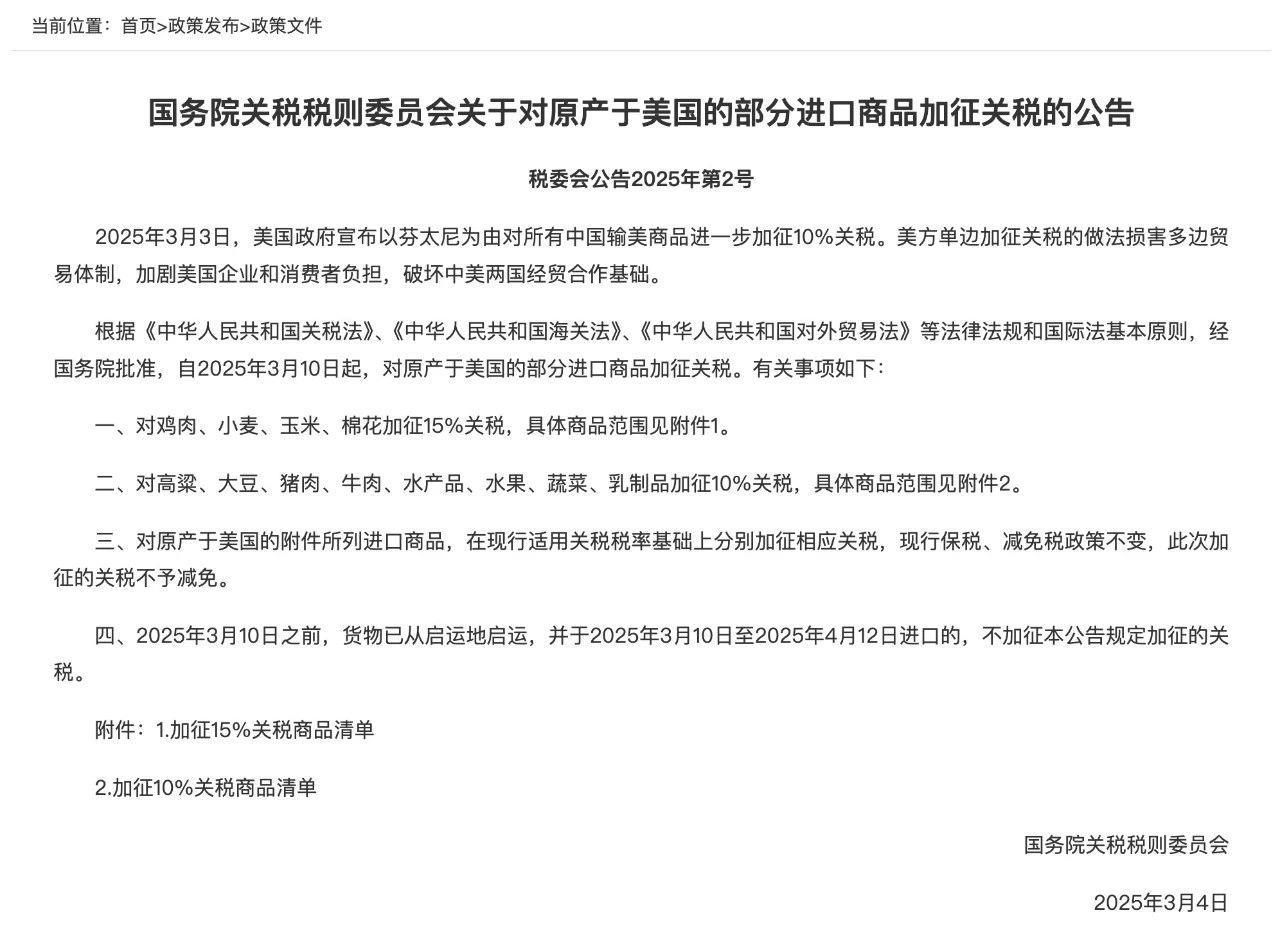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9
京ICP备2025104030号-19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